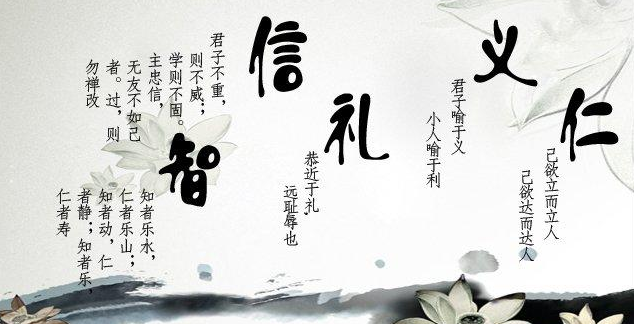
其实,我们仔细一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都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这个特征不假。但中国人处理内在矛盾的方式和日本人处理这种内在矛盾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中国人用的是“变通术”。有矛盾不假,但我们可以统一在自己身上。需要这个用这个,需要那个用那个。矛盾的两极,出现哪一极,由自己选定。于是,一个人有两张面孔,一件事有两种说法。说起话来,“尽管……但是……”这样的语法结构频频使用,模棱两可、见风使舵之人大行其道。权术玩到极致,精明成了国粹。
日本人用的是“分离术”。他们将不同的属性置于不同的场合下。根据不同的场合,大家强调不同的标准,而不是让个人决定采取何种对策和表现。
所以,当他们视你为一类时,他们强调对你的仁爱。他们视你为另类时,他们对你无情可言。
当你在生产过程中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时,服从成了你必须表现的品性。而当你在生活中消费时,尊重成了你一定能得到的奖赏。
在权力、身份上,他们强调等级秩序。在收入分配上,他们强调平等和谐。
这种“分离术”和我们的“变通术”有何优劣之分呢?
“变通术”尽管统一了矛盾,但把选择的权力给了个人,让个人根据不同场合下的自我需要,变通决策。后果就是管理的原则得不到坚守,管理的真相无人知晓,管理的措施完全被个人化解。最终的结果就是:一盘散沙,三条龙成为了一条虫。

“分离术”也保持了矛盾。但它让矛盾的两极处在不同的场合,避免了互相干扰,杜绝了个人选择。
因为尽管在不同的场合,他们的行为看似矛盾,但在特定的场合,他们是必须按一个标准做的,个人没有选择余地。这就为现代管理最需要的原则性、标准化、执行力提供了文化和习俗的有力保障。
在日本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分离术”的运用,让他们很好地实现了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
在人的精神和思想领域,他们更多的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在人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领域,他们更多的吸收了西方的机制。这种精神与行为的分离、人与事的分离实际上是为东方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提供了一个示范,一个成功的社会案例。
如果说,日本企业家的确说过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话,我们倒不妨把这个“算盘”理解成一种数量化的管理思想和模式。就这一点来讲,恐怕他们心中的“算盘”早已经是西方的科学管理了,而不是中国古老的“算盘”概念。

由此可见,这个一手拿《论语》和一手拿算盘的说法,其实就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之意,只不过他们是两只手“分开”拿的。
不像我们给了人家《论语》的人,还一手既抓着《论语》,又抓着算盘。另一只手在干什么呢?在比划着如何去变通。悲哉!
其实,看一看中国的近现代史,历史上中国现代化的哪一次巨大的进步,不是与这种“分离术”的采用相伴随呢?
毛泽东创造性地在军队设置了管人的思想和军事的两条线,让人与事相对分离,创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中国现代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基础。
|